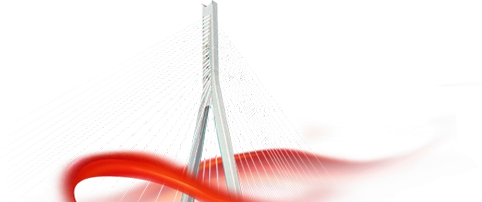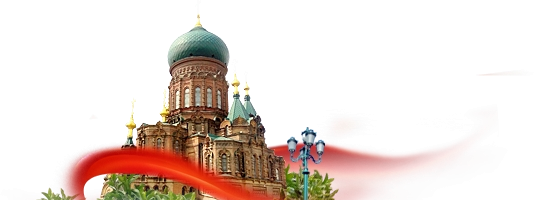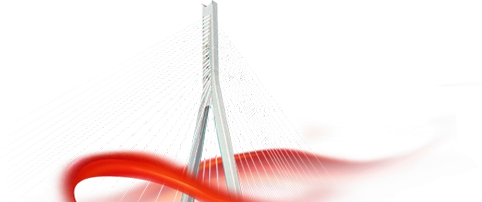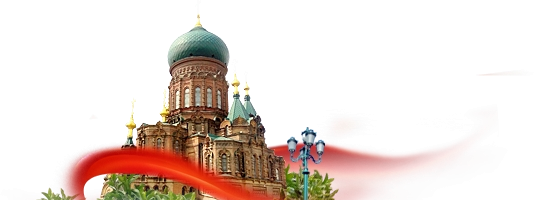(陈明)父亲生前常常提起,1963年秋天,因为铁路部门合并,我们全家从牡丹江迁到哈尔滨。那一天,15辆手推车从铁路货运门一路蜿蜒至海城街2号,那上面装着我父亲——一个铁路技术人员的全部家当:一对儿斑驳着“美满家庭”字迹的木头箱子,两个柳条包,还有刷不净的碗架柜、小饭桌、锅碗瓢勺和木头床木凳以及木头柈子、煤、炉筒子等等,此外还有他的从六岁到十三岁不等的四个孩子和一个瘦瘦的满身是病的老婆。
旅途很累,我只记得自己错头涨脑地同一堆破烂一起被从手推车上卸下来后,头一挨到什么硬东西便睡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在一片红光中醒来,遂带着几分惊奇走出这个陌生的新家,发现这里周遭有着罕见的幽静。穿过墨绿色的俄式木栅栏,蹚过野蒿,蓦然出现在十几米外的,竟是一条清清亮亮的河。生在都市,长在都市,看惯了楼房、水泥路的我,一下子竟弄不清是我依旧在梦里,还是河水的梦中有我。
河水一望到底,水中手指粗的小鱼密密麻麻成团成阵地在水草中移动,蹲在湿泥上两手放在水里一掬,就有两三条小鱼在掌心跳跃,痒痒的。两岸是齐腰的蒿草,人往里一走,碧绿碧绿的青蛙比着高往水里跳,水面响起唰啦啦的声音。红翅膀、花翅膀的晴蜓腾空而起,遮天蔽日,把空气都搅成金色的;蜜蜂在野花丛中嗡嗡嘤嘤;巴掌大的马莲蝴蝶,雪片一样的白粉蝶从脸前拂过,我好像伸手就能抓到,又连连扑空,急得蹲在草丛中小声唠叨;蝴蝶蝴蝶落一落,我给你板凳坐一坐……
蝴蝶没有落,却发现了草丛中已经成熟的一串串紫色的“天星星”,摘下一串放进嘴里,甜甜的,凉凉的;小红灯笼一样的野菇儿一片片熟在那里,撕开外皮,掌心里赫然是一颗透明的玛瑙……
我玩疯了。直到天色渐暗;直到听见母亲的呼唤;直到我姐我哥一人一个膀子把我从草棵子里薅出来,布鞋上沾满了叫“刺球儿”的草籽儿,一根小辫子不知什么时候被野荆拉散了,下半拉脸和舌头都被“天星星”染成了紫黑色。向左看,一轮斜阳正挂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主楼的尖顶上,右边,尼古拉教堂的钟声顺着河面一波一波地荡过来……
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是什么缘分让我九时来到这条都市里难得的河边,并且一住就是23年。随着岁月经历和知识的积累,我逐渐地渴望更深地了解她。有文字说,这是一条天然形成的集雨河,雨水多时她就深一些,雨水少时她就浅一点儿,很久很久以前,连“哈尔滨”都不知为何物时她就静静地流淌着。1896年的《拉林舆地全图》和1897年的《黑龙江舆地图》中,她被标出马架子沟、马家沟的字样。据说,“马家沟”一词的由来和俄语标音有点关系。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而“联俄抗日”这一饮鸩止渴的主张使觊觎中国良久的帝俄以“中俄合办铁路”为名堂而皇之地开进来。当年在这条河的下游,即今天的奋斗路桥西侧有一个叫“马架子沟屯”的小村落里,住着几户渔民,他们依江傍河,悠哉度日。之所以叫马架子屯,是因为他们终年住在一种用人字形木架搭起的窝棚里,棚顶是柳树条子、小叶樟草和泥坯,屋内是用桦木、柞木搭就的地铺,地中间的炉灶烧着木柴,既能取暖又可做饭。俄国人来了以后,为了连接道里、南岗和香坊的通道,在这条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用俄语根据马架子沟标音,汉语便叫成了“马家沟”,从此便刻印在哈尔滨的版图上。这条不断的链条起源于哈尔滨平房区东南安家窝堡屯与阿城交界的王惠文屯,她连接着平房区、动力区、南岗区和太平区,穿越两座铁路桥,14座公路及市街桥,挟哈尔滨动物园和儿童公园两幅如画的风景,最后在松花江滨北铁路大桥下注入松花江。当年的俄国人在河边修筑了很多精致的小别墅,上世纪60年代初期,很多当年的中东铁路员工还住在那里,便有了我的不少“二毛子”“三毛子”同学。每到春季,俄罗斯小别墅院里开满了紫色的丁香和海碗大的芍药。帝俄的统治者播下了罪恶,勤劳的俄罗斯人民却栽种了文明。我的在铁路局、原中东铁路管理局大石头房子供职的父亲,每天早晨沿着河边小路去上班,晚上像当时的列车一样准时地出现在小路尽头。他的手里有时拎着一个蓝格手帕系着的小包,那里面通常是几个又黑又丑带着麻点,却一咬一股又酸又甜的水儿的安梨,或者是一包“毛子嗑儿”。当然,那样的时候不多,于是,盼到了手绢包的日子就成了我的节日。
在这都市里的乡村,我们学会了把鸡撒在草丛中散养;学会了在河里放鸭;学会了在封冻的河面上打爬犁,从坡上往下打,一出溜到对岸;学会了用洗衣盆和小米粒儿在雪地上扣家雀。我们做这些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穿黑衣服、戴红胳膊箍儿的高高大大的老人在一旁微笑着倒背着手看热闹,他是这一带的护堤员,别看面善,你敢随便从堤上撮一锹土他都会追到你家让你送回来。他常常告诉我们,要爱护这条河,以后,政府还要把这条河加宽,两岸栽上垂柳,把松花江引进来,那个时候你们一出家门,就能划着船去松花江了。河边的孩子们做梦都盼着。
可是渐渐地,我们发现了变化。最先觉得蹊跷的是护堤老人突然不见了,随后河里的小鱼一片片死去,翻出白花花的肚皮,一清到底的河水逐渐呈深绿色,一股股刺鼻的怪味儿一天比一天强烈。然后是家家放养在河里的鸭子集体不下蛋。更奇怪的是,邻居家褐麻色母鸭不但拒不下蛋,而且渐渐长出蓝色的硬翎,叫声也一天天沙哑起来。母鸭变公鸭,打死谁也不会让人相信,这都是些什么兆头。一急眼,家家户户发一声喊一齐杀鸭子,原打算吃肉算了,可是一开鸭内脏全傻了眼,个个鸭子肝部出奇地肿大,肝甚至占据胸腔的三分之二。大人们咬牙切齿,在孩子们的眼巴眼望中,把鸭子的尸骸统统扔进河里。有一天,从上游漂下来一团黑黑白白、花花绿绿、毛茸茸的东西,孩子们不知是什么妖怪,成帮结伙追着打,这东西在如雨的砖头中翻上翻下,一会儿伸腿、一会儿展袖、一会儿摇头、一会儿摆尾,连大人都看傻了,大着胆子捞上来一看,是一团纠缠不清的戏装,朝靴、长髯、龙袍……上好的戏装啊,怎么都扔掉了……
那是1966年位居河上游的京剧院扫“四旧”,荡涤下来的“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失去管理的马家沟被56座工厂、4家传染院围绕,123处废水排放口以每日数千吨的流量向河里排放。河水里充满了砷、汞、铬、铅、锌等重金属有害有毒物质和病毒细菌等病原体,这岂是鸭子能抗得住的。马家沟河从此变成了一条不冻的污水河。冬天,当北国大地冰封雪裹时,只有她,冒着灰腾腾的雾气黏稠地流淌着,刺鼻的异味儿熏得人头疼,长相怪异的蜗牛恐怖地蠕动着——马家沟,成为哈尔滨这座城市肌体上一道终年流脓淌血的不愈的伤口。
而河边长大的孩子也远离了她,更热衷于戴着红袖标去冲击政府,贴大字报,上街游行……尼古拉大教堂被推倒了,从河面上荡过来的不再是钟声,而是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两岸的垃圾很快就堆积如山,山上常常出现一个黄头发、长裙的剪影,那是我的“二毛子”同学的被遗弃的苏联妈妈……一个俄罗斯贵州的后裔在捡破烂……而我的在铁路局大石头房子里兢兢业业当工程师的父亲也被当作“反动技术权威”赶了出来,上铁路小学去烧锅炉。有一天,我在一片“黑五类狗崽子滚出去”的叫喊声中滚出了教室,正好碰上赤裸着瘦弱的脊背的父亲担着两筐炉灰从地下室的锅炉房里爬出来。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哭,只觉得心底有一股清水忽地一下被泼脏了。从此,那个散着一根小辫儿,吃得满嘴黑紫色的小姑娘永远地消失了。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因伏案过久而弯了腰的父亲光荣地离休了。同时,这位画了一辈子高楼大厦的高级工程师也终于乐不可支地住上了自己设计的新楼房,离开了住了23年的阴暗潮湿的河边小院。可是那条小河却永远留在了我的梦里。当我接触到了文学,觉得自己的笔尖在不断地涂鸦中逐渐硬朗起来的时候,我写的第一篇体面一点儿的作品就是《小河从市区流过》。这是一部电视文学脚本,用儿童的眼光描述这条河,以及对她的爱和恨,作品意外地得了个黑龙江电视台的佳作奖。奖项并不辉煌,也没人给投拍,可是,我却像皇帝爱长子一样地钟爱它,我把剧本念给我的父母听,他们沉默不语……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给哈尔滨这座百年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了令人瞠目的变化,马家沟这道城市躯体上的创伤愈来愈刺人眼刺人心让人不能容忍。市政府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开到河边,拓宽河道,堵截污流,修整两岸,栽树筑堤,一条带状公园的雏形逐渐清晰,那个戴红胳膊箍儿的护堤老人的童话似乎真实起来。
转年又到了一个春天,我想,马家沟河的治理改造必将会牵涉到我的小院,我应该去留下点什么。当我带着照相机旧地重游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百感交集。我住了23年的小院早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高楼群立,可是几经治理的马家沟堤岸设施竟在一个冬天里被践踏得面目全非;破败的花坛、缺损的堤石,两岸垃圾挟沙飞扬,依然有人肆无忌惮地往河里倾倒污水。难闻的气味儿中,我任风梳理着思绪,旧情不要重温,旧地不要重游。至理名言啊,我还是走了吧。我捂着包里的照相机落荒而逃。
以后的忙忙碌碌的岁月,把我和河边的距离越拉越远。可我却十分关注报纸上对破坏马家沟河新设施的谴责,和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治理,甚至从河底清除百年污垢,我仿佛听到了城市伤口逐渐愈合的声音。我的小河情绪逐渐地平衡下来。我不再害怕面对现实,就像不再害怕触及伤痛一样。前几年,我曾来到过河边。这里又有了整洁的堤岸,精美的围栏、草坪、绿柳、古榆,令人耳目一新。当年的俄罗斯别墅正从棚厦中被清理出来。按照市政府规划,整个当年的“马架子屯”要建成“俄罗斯风情园”。虽然这还需要过程,但我们毕竟开始了。我在一个个旧式建筑中走过,明知不能,却依旧寻找着我的“二毛子”“三毛子”同学,寻找着丁香树和芍药花。在一座河边凉亭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正和几个老人打牌的中国装束的苏联老太太,我认出那是我同学的母亲,当年那个垃圾堆上的俄罗斯公主,她居然和那些遗迹一起幸存下来。
站在河边,我闭上眼睛,眼前一片红光。我似乎又回到多年前那个下午,我在一片红光中醒来,梦游般来到河边,野蒿、清水、小鱼……悠悠的钟声中,我在河边盼着我那擒着蓝格手帕包的父亲……
作者:市政协第十至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市文联作家协会副主席